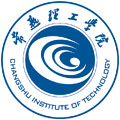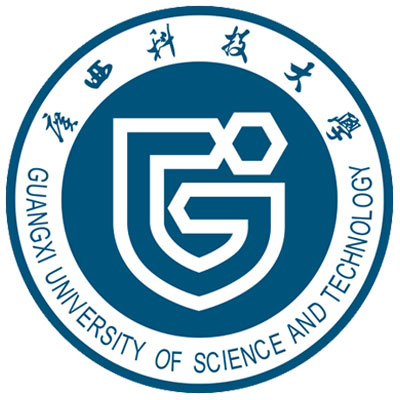■康绍忠
康绍忠
1978年7月参加高考,1978年10月进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农田水利工程系学习。农业水土工程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常委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业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会长、高等学校农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Frontier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执行主编。在干旱区农业高效用水与水资源领域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先后获ICID国际农业节水技术创新杰出成就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优秀科技图书奖三等奖1项,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项。2010年被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完成高中学业,要么回农村老家继续种地,要么去中学担任代课老师,是高考的恢复改变了我的命运。其实,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农家子弟的命运,更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命运。
幼年的经历让我对农业水利有了最直接、感性的认识——只有保障干旱季节的灌溉用水,农作物才能丰产。因此,在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当时多数人“远离”的带“农”专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工程专业。
“半工半读”完成中学
1962年11月,我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的一个农村家庭。那时还有公社,我们涌泉公社有15个大队,我家所在的大队叫新民大队。我父亲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当年我们大队只有小学,没有初中。父亲很重视办学,多次跟公社领导争取协商开办中学。在他的努力下,我们村最终办起了初中,我所在的新民小学升级为新民中学,周围6个大队的孩子也都来我们大队上初中。
我是1969年春天上的小学,正赶上了“文革”。到我上初中时,已经是“文革”后期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半工半读”,上午在学校学习、下午去生产队劳动。后来学校里也在山坡上开挖梯田,我们也经常前去干农活。
初中两年我一直担任班长,直至1976年步入高中。按照政策,那时实行分片上高中,我们新民中学的学生一半去了漆河镇里的桃源县第四中学,一部分去公社的涌泉中学高中部。我在桃源县第四中学就读,并在高一年级担任班长。
刚入学的第一年,我们还是处于“半工半读”状态。除了在学校的农场里干活,还要去对口支援的大队新建的居民点,帮助挖沙子铺路,修水库等。1977年上半年,我们的劳动还十分繁忙,晚上有时候也要前去,但当时每个人都热情高涨,干活积极卖力,并不觉得很辛苦。
其实,读高中之前根本就没考虑过上大学,当时的想法是好好念完高中,有机会招工当一名水利工程管理人员,或者到县上棉纺厂当工人。
根据墙上广告选取专业
高一那年,听到广播里说全国恢复高考了,同学们特别高兴。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我成为学校从200多位高一学生中推荐提前参加高考的两名学生之一,参加了1977年冬天的选拔考试。但遗憾的是,我们两位因为没有系统学习过高中知识,也就没有考上。
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学校重新分班。这次分班源于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我清楚地记得郭沫若发表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里那句“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当时学校有4个班,后来学校把4个班的尖子生集中到一个班,我也就从原来班的班长变成了尖子班团支部宣传委员。1978年上半年,老师集中加班给我们复习,准备7月的高考。
那时的高考不像现在,没有父母陪送。考试就在我们中学的教室里,可能因为我年龄小,再加上高一考过一次,并没有感到紧张。考完后,我一个人去县城体检,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县城。
过了一段时间,分数才下来。我考了352分,在所上的高中算分数最高的前两人了。当时我们桃源四中那一届也就考上七八位,包括后来补录的大专生。
那年全国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第一批录取比例仅4.8%,在偏远农村中学要考上大学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填报志愿时,因为那时信息比较闭塞,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无意间在学校墙上看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招生广告,宣传广告上有一条高压输电线、一座水坝。由于我对这种场景十分熟悉,并且抱着一种学成后为农村水利事业服务的朴素愿望,所以毫不犹豫就填报了这所学校唯一一个带“农”字的专业——农田水利工程。
其实,这样的选择还与我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桃源县是当时全国有名的水利建设和水利管理先进县,具有丰富的水资源,星罗棋布的水库、水电站、排灌站等水利设施。小时候我经常手拿镢头、钢钎,和老人们一起修水库、修水渠、建排灌站,这种体验使我从幼年便对水利工程有了最直接和感性的认知,也切身感受到了家乡的丰饶物产得益于水,只有把水“用”好了,农作物才能长得一年旺似一年。
我被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工程专业录取后,才知道这个专业极其冷门,很多人不愿意选择,因为它带“农”字。特别是有些城里来的学生认为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却又走进了“农门”。
去校医院看病,有的同学就怕大夫问起学习什么专业,因为专业带“农”怕别人瞧不起。然而我对这个专业并没有偏见,因为当时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学习水利知识,为发展农业生产作贡献。
高考完后我在家里等分数,也不知道能不能被录取。当时也有点着急,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当时公社联校的校长找到我父亲,想让我去涌泉中学担任代课老师。这是由于我初高中成绩都比较好,尤其是小时候记忆力强,全公社开中小学老师大会时,让我作为典型在会上背诵毛主席语录,在场的100多位老师任意挑选一条,我都能准确无误背下来,校长对我的印象特别好。
命运出现了转折点,不久我顺利收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没有前去做代课教师。
现在想想,如果不是高考,我将有两种命运:一是在农村老家继续种田,二是去公社中学当代课老师。
书包锁在凳子上占座
学校因多年未招生,教学楼、宿舍楼等基础设施都要重新维修整理,1978年10月6日至7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终于迎来了新生报到的日子。我于10月6日前往东湖之滨、珞珈山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
学校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很好地解决了我生活上的困扰,可以一心一意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畅游。当时学校给予我们大部分同学助学金,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分为甲、乙、丙等。我是最高的甲等,每个月20元,其中17元是饭费、3元是零花钱。开始时饭票上标有早、中、晚餐,不吃就作废。后来同学们都很有意见,记得大二时就改成只标有钱数的饭票了。
我们班同学间的年龄差距非常大,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被称为“老三届”,最小的是1963年。我是1962年出生,算是班里倒数较小的几位,入学时还不到16岁。“老三届”非常不容易,他们有的人等了十几年才有上大学的机会,其中我们班的“老大”上大学时已经有3个孩子了。所以他们学习十分刻苦,这也极大地鼓舞与激励了我们。
我记得,当时的数学教材为同济大学主编,分上、下两册。60%以上的同学除了把老师布置的教材习题做一遍以外,还会主动把樊印川的《高等数学讲义习题集》里的习题再做一遍,这是一本“文革”之前的大学数学教材配套的习题集。
那时候学校没有太多的文体活动,同学们大多去图书馆或大教室学习。但因刚恢复高考,图书馆的学习室非常狭小,座位有限且珍贵,如果去吃饭要离开一会,必须要占座。一般情况下,书包仅仅放在凳子上占座是不可行的,因为回来时书包有可能就不在原地了,必须把书包锁在凳子上。所以,同学们的书包里经常会装一把锁。
那时,我们一心只是想着好好学习,希望日后能为国家作点贡献。
科学报告会上唯一本科学生
我们上大学时学校的学术交流活动不是很多。记得大概是1981年的秋天,我看到农田水利教研室有个学术报告会的通知,内容涉及地下水资源动态评价、组合喷灌强度计算、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
我出于好奇与兴趣,兴冲冲地跑去聆听。但到了教室才发现,近40人的科学报告会只有我一人是本科学生,其余都是老师。
老师们坐定后,教研室秘书给每一位老师发了一份有十几页的组合喷灌强度计算的油印材料,可能知道我是学生,加之也不认识我,唯独没有给我发那份材料。
这时在我前面一位和蔼可亲、看起来十分有学问的老师看到此景,就对秘书说,大家都发了,也给这位同学一份吧!顿时我内心无比激动与感恩,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蔚榛老师。
张蔚榛老师是上世纪50年代中从苏联获得农田水利副博士学位后回国的,是十分受同行尊敬的我国著名的农田水利与地下水专家,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老师为人和善,他不仅给予年轻人关心和提携,在学术上更是一丝不苟、严谨治学,在如今浮躁的学术大环境下却很难再找到这样的老师。他是我十分崇敬的老师,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我在工作后跟张老师一起参加过几次成果鉴定会,鉴于我国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凡是材料上写着“国际领先”字眼的,张老师都谨慎签字。
大学时期对我影响很大的还有茆智老师。他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在灌溉工程及其用水管理的理论与技术方面有出色成就,现在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那一届,茆智老师指导四个本科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茆老师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办公桌,我们每周都要去他家围坐在办公桌前汇报和讨论毕业论文进展。
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水稻需水量的分析与计算”,茆老师亲自带我们到安徽滁县水文实验站等地调研收集资料,分析早、中、晚稻生育期需水量的变化规律,以及需水量与品种、空气温度、湿度、日照时数和栽培措施等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茆老师悉心的教导与关心,使我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并获得优秀。也正是由于此次经历,让我更加喜欢上了作物需水量研究,并逐渐扩展为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水分传输和作物节水调质高效灌溉理论与技术研究。
可以说,大学教育对我的职业选择影响比较大。1982年,我抱着要进行农田水利与土壤物理、作物学相交叉领域研究的梦想,考取了原西北农业大学(后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的硕士,随后又攻读了博士学位。
1993年9月,我被西北农业大学破格晋升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1994年入选了中国科学院首批“百人计划”,1997年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1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科学成果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唯有长期积累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这是我时常激励自己的话语。
2002年,我调入中国农业大学工作。但最近10多年我们团队的工作仍然扎根在西北旱区,我们团队建设的中国农业大学石羊河实验站,常年有60~70位师生住站研究和实习,已成为西北旱区农业节水技术示范推广、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的重要基地。目前我们的研究又扩展到新疆南疆等区域。
一路走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平凡普通的人,有时甚至感觉还有点“愚笨”,但我们那一代人,都是靠自己的奋斗与汗水浇灌出梦想与希望的。我想,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艰苦奋斗、严谨治学、持之以恒和团队精神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最需要培养的。
(本报记者秦志伟采访整理)

①康绍忠(后排左三)高中毕业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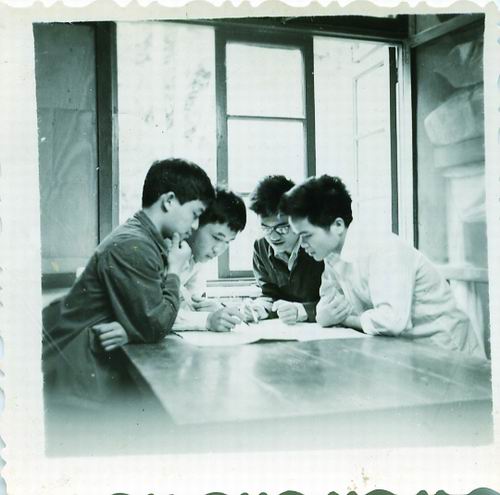
②康绍忠(右二)和大学同学在宿舍讨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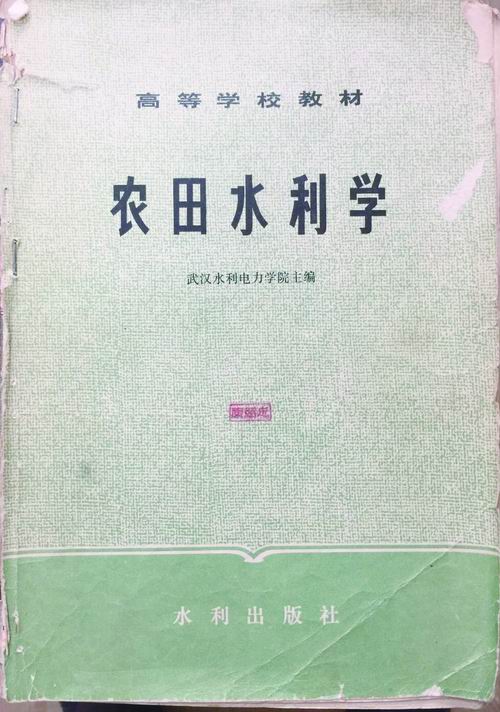
③当年的大学教材
中国-博士人才网发布
声明提示:凡本网注明“来源:XXX”的文/图等稿件,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及方便产业探讨之目的,并不意味着本站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文章内容仅供参考。